李景平,《中国环境报》高级编辑,山西省作家协会生态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著有《绿歌》《20世纪的绿色发言》《走过时光》《风在心间行走》《云下山河》等。获中国新闻奖、中国环境文学奖、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赵树理文学奖、《黄河》年度文学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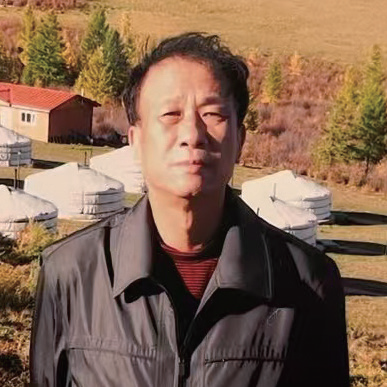
肖亦农,作家,河北保定人。内蒙古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曾创作中篇小说《虹橄榄》《灰腾梁》、长篇小说《穹庐》;创作生态文学报告文学《绿色壮歌》《人间神话:鄂尔多斯》《毛乌素绿色传奇》。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
李景平:肖亦农老师好。最近在媒体看到,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被称为“中国沙漠治理的又一壮举”。在中国作家中,你是早就以书写沙漠生态治理而闻名的生态文学作家。你的生态文学书写大多聚焦于鄂尔多斯的沙漠生态治理,沙漠生态治理是怎样引起你文学关注并开启文学书写的?
肖亦农:鄂尔多斯曾是一片被黄沙覆盖的土地,如今已变成全球荒漠化治理标杆。其标志性事件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3次缔约方大会,于2017年在额尔多斯举行,发布了《鄂尔多斯宣言》。这个宣言肯定了鄂尔多斯“沙漠绿色经济”模式,旨在推动“绿富同兴”,强调政府领导,多方合作,动员社会化力量共同治理荒漠化,在2030年前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这一壮举,证明鄂尔多斯治沙具有现代化国际水平,为世界荒漠化治理提供了一个“中国样板”。
20世纪60年代,我在知青时代就进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当时,鄂尔多斯还是一片沙漠,人在沙漠,常常窗外狂风乱作,黄沙飞扬,屋里尘土弥漫,落满细沙,吃饭嘎巴嘎巴嚼着沙砾。后来我到了交通部门,天天修路护路,其实就是天天和沙漠较劲。我当时慢慢的开始写小说了,虽然感受到了沙漠对人的威胁,但不知道这是生态环境问题,即使写小说写到沙漠种树,也没认识到是生态环境保护,没想到把生态环境问题放到创作中,更没想到人能改变沙漠。
沙漠对于外人来说是新鲜的,对久居沙漠的人却是十分无奈。后来,沙漠上的人和事,教会我认识人与沙漠的关系。我当时在公路养护道班上班,偶有牧民路过道班歇脚,就教我们怎样防沙,怎样在院墙四周种树、怎样在院外种植苗圃。生活在大漠中的人摸索了许多生存技巧,这让我感受到,只要和沙漠抗争,还是能战胜风沙的。我们在公路养护中汲取了牧民经验,终使小小道班被交通部命名为“红旗道班”。我以这个素材创作发表了小说《灰腾梁》《山风》,并被《小说月报》转载,成为我早期创作的代表作。
我真正介入环境文学创作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虽然当时我已经写了沙漠治理的题材,但我并不知道环境文学是什么。创作完全源于我对沙漠治理的深刻感受和对治理工程的浓厚兴趣。当时,鄂尔多斯正启动一项巨大的沙漠工程:“两翼一体”战略和“3153”工程,铺开治理鄂尔多斯东部的砒砂岩山地、西部的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漠。这么大的工程,是鄂尔多斯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做过也没有人敢做的事情,我当时以极大的兴趣选择了对治理工程的书写。
之后,我跟踪鄂尔多斯生态治理历程近40年,经历了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治理历史,见证了鄂尔多斯生态环境保护的艰辛。我在环境文学或生态文学的书写中,发现了鄂尔多斯,也发现了自己。我觉得,写环境文学或生态文学,是一种注定,我希望我的环境文学或生态文学作品,不仅记录鄂尔多斯生态治理的历程和成就,也传递一种生态理念,使更多人懂得生态治理的重要意义,从而激发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行动。为此,我被称为生态文学作家。
李景平:鄂尔多斯治沙行动和你对治沙行动的关注,在时间上,恰好也是中国环境文学起步并逐渐勃兴的时期。当时,中国许多作家应环境保护部门的邀请,开启了中国文学界的“环境文学行动”,曾一度掀起中国的环境文学热。对于当时中国文学界的环境文学热潮,你有印象吗?
肖亦农:我的生态写作,与沙漠治理同步,也几乎与环境文学同步,只是开始生态写作的时候,我还不知道环境文学的概念。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十月》杂志主编张守仁到鄂尔多斯考察,我第一次知道了环境文学。张守仁此行的目的是考察生态环境治理,他对砒砂岩治理和沙漠治理很感兴趣。我当时并不知道张守仁的来访目的,只想着他对这片土地和它的环境治理充满兴趣,我陪同他进行了考察。当时我已经离开沙漠回到城市。我陪他看了一棵树。这棵树是我在沙漠时亲手种的,我在树上还刻了一行字。多少年过去,我带张守仁找到这棵树时,树已长到碗口粗,我刻在树上的字还依稀可辨。看到自己种的树,看到自己刻的字,我不禁泪眼婆娑。
就在这时,张守仁向我透露了他的另一个目的,他正和一群老编辑创办一个刊物,专注于环境文学作品的发表。这应该就是后来创刊的《绿叶》。张守仁说,这个刊物将汇聚国内著名文学编辑和作家,一同推动环境文学发展。他说,尽管过去文学也反映社会问题,但环境问题作为紧迫的社会问题,直接关乎人类生存发展,更应成为文学反映的问题。他预测,环境问题将成为未来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我当时对环境问题不熟悉,听起来懵懵懂懂,但张守仁的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开始关注环境文学,思考环境问题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正好这时,鄂尔多斯启动了“一体两翼”战略。
如今再看,正如张守仁先生所言,环境问题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环境文学也迎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前途。自那以后,在我的脑海中,环境保护概念和环境文学概念清晰起来,我再回头看鄂尔多斯,无论是东部的砒砂岩还是西部的沙漠,在我的认识里概念完全不一样了。鄂尔多斯这片山地、这片沙漠,看似不适合人类生存,实际上,鄂尔多斯人早就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开始了独特的治理之路,譬如小流域治理、砒砂岩治理、荒漠化治理,那都是鄂尔多斯人寻找生存、生产、生活之道的生态修复工程,是一项生命工程。这时,我已经清醒地知道,我要写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了。
于是,我深入鄂尔多斯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从荒凉的沟壑到漫天的黄沙,我见证了鄂尔多斯人为治理环境所做出的艰苦奉献,与许多基层干部和普通劳动者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基于实地采访和体验,1990年,我连续创作了多篇关于鄂尔多斯环境治理的报告文学。一篇名为《准格尔倾诉》的作品,记录了鄂尔多斯人在“3153”工程上的奋斗历程和成果。作品一经发表,就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领导不仅对作品给予高度评价,还提议我进行深度探索,将鄂尔多斯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故事传播得更高、更远,鼓励我与中央报刊合作,让中央层面关注鄂尔多斯在沙漠治理和生态保护上所做的事情。
我满怀激情投入鄂尔多斯大地实践探索,跑治沙工地,住施工工棚,吃在沙漠,写在沙漠,很快又完成报告文学《绿色壮歌》。这篇作品记录了鄂尔多斯沙漠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奋斗英雄和辉煌历程。我将作品投稿给《人民日报》,得到编辑的青睐,报纸用了整整一个版面予以发表。《绿色壮歌》的发表,不仅是我个人环境文学创作的里程碑,更标志鄂尔多斯环境与文学之间有了一种紧密的联系。从此,在鄂尔多斯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环保与文学之间,环境文学与环境治理之间,我的文学创作与沙漠治理之间,总能产生某种奇妙的共鸣。这时,在我的自觉意识里,我的创作慢慢的变成了环境文学创作。
李景平:你之前是以小说创作获誉文坛的,在当时的环境文学写作和后来的生态文学创作上,为什么选择了报告文学作为创作主攻方向?这与和你几乎同龄的作家哲夫有所相似。哲夫也是由小说创作转向生态环境小说创作,又由生态环境小说创作转向生态环境报告文学创作的。
肖亦农:哲夫先生确实是一位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家。作为一位作家,我深感选择恰当的文学形式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变迁的重要性。书写鄂尔多斯这一特定地域的生态变化,我选择了报告文学,是因为我觉得它能够最直接、最迅速、最鲜活地捕捉并反映这种变化。
当然,我也并非一开始就自觉地意识到报告文学在反映生态变化上的优势,而是在创作过程中逐渐体会到其独特魅力。报告文学作为一种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体裁,它不仅要求真实还原事件,更强调文学性的表达。对我而言,也是给自己提出一个实践命题:如何保证在非虚构真实性的基础上,赋予作品以文学性和生动性?
文学性无疑是报告文学的第一要素。可以说,鄂尔多斯生态环境治理的火热第一线,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对于奔跑在第一线的作家来说,从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来讲,我采访到素材是不成问题的。那些事迹,本身就具有触动人心的地方,但假如没有文学性的升华和深化,充其量只能算新闻报告或通讯报道,无法深切地打动人心,也无法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我的创作始终将文学性放在首位,力求通过细腻的笔触、细节的描写、形象的塑造和深刻的思考,将鄂尔多斯生态变化的真实面貌生动地呈现给读者。这就是我选择以报告文学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变迁所追求的独特价值。
报告文学作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文学功底,更要有深入生活的勇气和毅力。我觉得,我只要有了自己的环境文学初心,这初心就如同鄂尔多斯人对待环境治理的态度一样,坚定而执着。对于创作生态报告文学,我也如同鄂尔多斯人在艰难中造绿一样,就像愚公移山,本身是一种深刻的磨砺。我在几万千米的行走中,采访、体验、思索,见证了鄂尔多斯人治理沙漠付出的艰辛和创造的辉煌。真实的治理历程和真情的文学抒写,融合、成就了生态环境报告文学之“真”。这是我深深感受到的报告文学的独特魅力。
应该说,我的环境文学或生态文学创作选择了报告文学的道路,但当我提及我的生态环境报告文学时,我深感它与郭小川当年在鄂尔多斯创作的报告文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郭小川20世纪60年代在鄂尔多斯写出乌审召人治沙的报告文学《牧区大寨》《英雄牧人篇》,我认为这算是环境文学的开山之作。
我的生态环境文学作品,则是他创作波澜之后掀起的又一个波澜。我们都为鄂尔多斯生态环境文学历史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郭小川的报告文学到我的报告文学,不仅记录了鄂尔多斯人在沙漠之地的奋斗,也都在鄂尔多斯文学史上留下了生态环境文学的鲜明印记。我为之感到自豪和欣慰。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能够说是我环境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此阶段我的文学创作作品有《虹橄榄》《灰腾梁》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环境文学创作作品有《绿色壮歌》等纪实文学作品。
李景平:能够准确的看出,你的生态书写,到《绿色壮歌》,已经由自发抒写到了自觉书写。从作家的视角而言,现实铺开如此波澜壮阔的一幕,确实应该大书特书。我想知道的是,采访这样空前的工程,你的采访是否得到空前的支持?因为涉及现实环境问题,官方持什么态度?
肖亦农:鄂尔多斯在沙漠铺开跨世纪的治理工程,可以说是历史性的、划时代的。我的环境文学或生态文学采访,也是我历史性的、划时代的采访。我始终受到鄂尔多斯高层的重视和支持。应该说,政府既然敢于铺开这样前无古人的工程,一定敢于让作家、记者宣传这样的伟大实践。
在20世纪末,我采访“一体两翼”战略工程时,当时的鄂尔多斯盟委书记陈启厚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告诉我,“一体两翼”是战略设计,“3153”工程是量化工程。量化工程规定了每一户农民在整个环境治理中的具体事情,譬如说建造多少标准田,建设多少水浇地,种植多少经济林,养殖多少猪和羊,等等。量化工程看起来“农民化”了许多,但动员农民行动起来,就得设立可操作、易执行的“农民化”指标,必须让农民直观地看到自己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和利益,从而投入这项伟大的生态环境战略工程中。他说,这样大规模的沙漠治理工程,必须发动农民这个主体。
21世纪初,我采写生态环境保护的时候,当时的鄂尔多斯市委书记云峰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和我做了深入的交谈,讲述了鄂尔多斯生态环境治理的政策措施。譬如,从每吨煤炭基金中提取特殊的比例的绿化费。这绝对是一个具有大格局、大眼光的创新举措。他说,鄂尔多斯作为新的资源型城市,必须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能一边治理荒漠,一边污染自然环境,而应该一手开采煤炭,一手修复生态。因而鄂尔多斯大量资金投入荒漠化治理,也投入采空区修复。他说过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话:“生态建设不仅关乎环境改善,更关乎老百姓幸福指数。一定要把生态建设融入老百姓的经济生活。”
在2011年采访创作《寻找毛乌素》的时候,我有幸见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当时,鄂尔多斯工业发展一举跃上内蒙古工业强市的前沿,沙漠治理也走在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前列。领导们说,我们不是单纯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也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论者,而是以现代生态文明思想和现代绿色发展思想为引领,推进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我深刻感受到了领导者对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洞察。他们对鄂尔多斯沙漠治理有远见卓识,对鄂尔多斯工业发展的决心坚定,他们的见解让我对鄂尔多斯道路有了深刻认识,也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灵感和思想。
可以看出,领导们的决策思路,前后一致。就是要让中国看见鄂尔多斯,让世界看见鄂尔多斯。应该说,这不只是是否支持作家创作和宣传的问题,而是执政者有没有执政能力和政治远见的问题。
领导们的热情和决心感染了我,我感受到了他们对农民的深厚感情和对环境治理的坚定信念,这也使我坚定了从事环境文学或生态文学创作的决心。他们为我的创作打开了采访的通道,也为我的构思拓展了思维空间。
李景平:你对生态文学书写这么有信心,并且信心这么坚定,那么,在基层采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波折?或者受到什么阻力?据我所知,生态环境新闻采访或者生态环境文学调查,因为涉及环境问题,在基层往往遭到阻挠,即使是从正面宣传报道出发,也往往遭遇尴尬。
肖亦农:阻力倒是没有遇到,但说实话,那时候人们对作家的认知,并不像对记者那样深刻。我到现场去采访,很多人觉得作家飘忽不定,心里没有底。我清晰地记得,日本老人远山正英带着他的协力团第一次进驻恩格贝,恩格贝试验区成立的消息吸引了众多人参观采访。我也去了,但我没有地方吃喝,没有地方住,处于如此窘境,我没有气馁,就独坐在大沙梁上仰望星空。我看着广袤无垠的大漠黄河宛如一条巨龙蜿蜒而过,想着恩格贝注入的新的活力,我顿时感到,这片古老的沙漠正呈现一种从来就没过的气息。
第二天清晨,我满怀期待地闯进了翻译的办公室,急于见到远山正英。我迫不及待地告诉翻译:“我要采访远山正英,希望你能配合。”翻译愣愣地看着我,疑惑地问:“你是哪个媒体的?”我微笑着说:“我是个作家。”翻译似乎对我的身份并不在意,态度却因我的坚持而变得友善:“好吧,作家先生,我陪你。”就这样,她领我见到了远山正英。整个采访过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没过多谈论自己的成就和荣誉,而是告诉我:“我是来赎罪的,替民族赎罪,弥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这种坦诚和谦逊让我深受感动。
他告诉我,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就是在恩格贝种下100万棵树。这个计划慢慢的开始,而且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远山正英的坚持和执着让我铭记于心。采访结束后,我被远山正英的精神深深打动。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环保人士,更是一位具有人类情怀和民族担当的智者。后来,他带着他的团队在鄂尔多斯种树14年,不仅改变了恩格贝的沙漠,更唤醒了人们对环保与和平的思考。这个人是真实的,这个人的故事也是真实的,他的整个治理过程更是真实的。如果我刚开始遭遇冷遇就退缩,我是抓不到这样真实感人的经典人物的。
李景平:鄂尔多斯的生态环境治理行动,引来了国外团队的参与,说明它的治理战略和治理工程是具有世界意义和国际影响的。在这场鄂尔多斯沙漠生态治理中,你又发现了什么样的中国式生态治理典型?塑造了哪个中国式的生态环境治理典型,并且是怎样塑造的?
肖亦农:采访体验中,我认识到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对于鄂尔多斯的重要性。这种认识反映在我的作品中,就是我更看重突出作品的环境意识和生态理念。但文学作品的生态意识和生态理念不是直接说出来的,而是以塑造具有生态精神的人物来反映出来的。因而,我的生态报告文学写作,特别注重突出生态人物和环保英雄的塑造。
鄂尔多斯8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曾经高达96%的面积遭受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恶劣的生态状况导致水资源极度匮乏,老百姓生活用水都按照时间表严格供应,到鄂尔多斯视察,宾馆连提供热水都成了难题。但是仅仅10年之后,鄂尔多斯成为一个生态环境优美、经济繁荣发展、百姓生活幸福的生态旅游城市。其生态治理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启示。
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青年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名为“英雄中国”的系列丛书,丛书之一是一部讲述鄂尔多斯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的作品。这部作品落在了我头上。我深知,书写这样一本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作品,是我的责任和使命。于是,我采访创作了《英雄中国:人间神话鄂尔多斯》,全景式地展现了鄂尔多斯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向社会呈现了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鄂尔多斯。
我有幸结识了一位杰出的生态治理者——殷玉珍。一个看似平凡却毅力非凡的中国女性,一位来自沙漠的巾帼英雄。我初见殷玉珍时,她正躬身在荒野,手握着铁铲子,在埋头种树。她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用铁铲在沙地上挖出一个又一个树坑,栽种一棵又一棵树苗,终于将6万多亩荒漠栽种成6万亩绿洲。这个成就背后,是无数个日日夜夜的付出和坚守、奉献与创造。她以坚韧的毅力,在荒漠化严重的土地上书写着绿色的奇迹。她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一群人的创业史,还是鄂尔多斯人的创造史。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我深感殷玉珍女士的伟大与不凡,特意将她的事迹写入《英雄中国:人间神线年,我受到了美国艾斯比基金会的邀请,前往美国访问。我特意带去了关于殷玉珍和另一位治沙英雄宝日乐岱事迹的书,以及她们治沙所使用的工具,旨在向美国人展示中国女性在生态环境治理上的卓越贡献。当我向美国基金会代表讲述殷玉珍和宝日乐岱的故事时,他们脸上露出了惊叹与敬佩的表情。美国朋友被这两位东方女性的坚韧与毅力所打动,对中国人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高度的赞赏。我还记得,当我展示她们所使用的治沙工具时,美国代表们都表示,这些看似简陋的工具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智慧与力量。我一直想向世界推荐我们的治沙英雄,这次访问,恰好给我提供了一个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巾帼英雄的机会。
由此,我深感自豪,因为我知道,殷玉珍和宝日乐岱的事迹和精神,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她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英雄,什么是线年,能够说是我生态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此阶段我的文学创作作品有长篇小说《黑界地》及中篇小说集《灰腾梁》;生态文学创作作品有《人间神话:鄂尔多斯》。
李景平:2015年秋,在太原举行的第25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我购买过你的《毛乌素绿色传奇》。这是一部获鲁迅文学奖的生态文学作品。据我观察,生态文学作品进入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评选并且获奖,当时是少之又少的,能够说是稀缺。那么,你的这部获奖作品是怎样诞生的?
肖亦农:在我的创作历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将生态思想正式纳入了我的作品。这是不同于我以往生态报告文学的地方。这一转变,不仅提升了我的人文意识,也让我对土地及其土地上的万物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感情。我开始意识到,生态文学创作不仅是关于生态环境的文学报告,更是对自然、对人类、对宇宙的一种世界观表达。
2011年,我从鄂尔多斯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得知一个消息:毛乌素沙漠即将消失!这消息如同一颗重磅炸弹,让我震惊不已。要知道,毛乌素沙漠是我们心中一片不可逾越的荒漠,它广袤无垠,黄沙漫天,让人望而生畏。毛乌素沙漠即将消失,我听了特别振奋!当年郭小川笔下的“牧区大寨”曾轰动全国,也仅仅是在茫茫沙海中种了微不足道的一点绿,毛乌素沙漠将会消失,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我曾在毛乌素沙漠地区工作多年,对那里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不等会议结束,就想着重返毛乌素。
我先后沿着四个方向进入毛乌素沙漠:东路、西路、南路、北路。从东路,我沿着国道和高速路前行,沿途的景象让我惊叹不已。原本荒芜的沙漠,如今已被大片大片的绿洲所取代,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向西、向南、向北探索,都看到了同样的景象:森林茂密,绿洲遍布,绿意如海,令人心旷神怡。我深刻感受到了毛乌素沙漠所发生的巨变。这不仅是一个沙漠的消失,更是一个生态奇迹的诞生。
站在陕北和内蒙古交界处的毛乌素沙漠边缘,我的心中充满感慨和自豪。这样的绿色奇迹,我不写,谁写?
我潜心研究了鄂尔多斯的历史与文化,试图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理解这片土地。这片内蒙古高原上的神奇土地,不仅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更孕育了无数生命与奇迹。我的头脑中逐渐形成对于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生态、哲学、现实、未来的发散性思维,一个全新的鄂尔多斯就在我的构想中渐渐凸显出来了。我于是意识到,在人类与沙漠的较量中,只有现代生态思想诞生,沙漠才能真的变成绿洲。
回望过去几十年的生态治理历程,我们经历了局部好转与整体恶化的交替,沙尘暴的反复肆虐让我们备感无奈与艰辛。过去,我们曾试图通过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来开垦土地,但往往面临着沙化反复的严峻挑战。头一年开垦的土地,第二年或许能迎来丰收,第三年又开始沙化,第四年便重新变成沙漠。这种被沙漠无情吞噬的现象,让我们深感无力与绝望。农耕的文明方式解决不了人类治理与沙漠复辟的矛盾和冲突。
只有通过现代生态科学的引领,我们才可以找到自然生态运行的规律,找到天人和谐的现代之道,也找到崭新的沙漠治理途径。诸如改善土壤技术、先进灌溉技术、防风固沙技术、植物种植技术、植被恢复技术,都是现代生态思想光照的生态修复与生态重建创新。具有了这种创新精神和创新开拓,就有了毛乌素沙漠的消失与毛乌素绿色的诞生。我决定将生态思想作为核心,将人文意识与土地情怀融入新的生态文学创作。
只有对土地有深刻的思想和感情,才能真正尊重土地上的万物,也才能向大地万物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深刻体会到生态思想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它不仅拓宽了我的创作视野,让我关注自然、关注人类、关注宇宙,也让我感受自然之美、生命之奇、宇宙之广,从而,以此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创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寻找毛乌素》,记录了一片沙漠的绿色转变和人类思想的绿色转变。
肖亦农:这部作品完成后,有幸全文发表在《中国作家》杂志上,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重视。内蒙古的出版机构迅速行动,将这部作品单独成书,命名为《毛乌素绿色传奇》出版,并进行了精心的包装和热情的宣传。
《毛乌素绿色传奇》出版后,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关注与认可,当时,由李敬泽主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组织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以及众多知名评论家如雷达、张守仁、李炳银等出席研讨会。副委员长布赫高度赞扬了鄂尔多斯人民用双手创造的人间奇迹。他认为,用笔将这一奇迹记录下来,引起社会反响,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可以说,创作《毛乌素绿色传奇》期间,我始终秉持独立、自由的心态。我深知,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其独立性和深度,而不是完成一个任务或迎合某种需求。虽然当地政府支持我的采访和写作,但提出与我签订合同时,我毅然决然地婉拒了。我认为,文学创作应该顺应内心感受,不受外因干扰。只有这样,才能让文学光芒熠熠生辉,展现出独特魅力。
我摒弃了一切商业的、遵命式的写作方式,坚持用自己的笔触去描绘毛乌素沙漠的绿色转变,表达我对这片土地和治沙者的深厚情感和深刻思考。所以,这部作品的独立性非常强,它有自己独特的声音、独到的见解和独具的思想。
我始终强调,文学作品的价值在于其独立性和深度。只有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才能够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正是我秉持独立精神、自由心态、深刻思想、科学价值,对文学创作理念的一次探索和实践。
虽然当时没有和地方政府有任何合同,但当稿子出来后,政府很看重,领导特别感动。政府党委第一时间组织了改稿会,邀请施战军、黄宾堂、关布、布仁巴雅尔、满全等作家、学者参加。大家提出了很多建议,我据此进行了修改。正因为地方政府和文学界、知识界的格外的重视,这部作品在2012年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2014年又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肖亦农:获得鲁迅文学奖之后,我收到了来自党委宣传部、乌兰夫基金会、鄂尔多斯市委以及自治区文联等机构的奖励和认可,这让我感觉到很荣幸。这些奖励不仅是对我个人的肯定,更是对生态文学创作价值的认可和鼓励。
其实,我最初并没想到能轻松的获得如此多的荣誉和奖项。我只是顺着自己的心走,用心去感受大自然,用文字去描绘它的美丽与变迁。能够将自己的内心感受与生态文学创作完美结合起来,我觉得这是土地给予我的一个最大幸运和奖励。因此,在获奖之后,我想了很多。
我想,《毛乌素绿色传奇》对我个人而言,无疑是我创作生涯的巅峰之作。它不仅记录了我对鄂尔多斯这片土地的深情厚谊,更见证了我对生态治理的关注与思考。这部作品让我深刻认识到,荒漠化改造是践行新时代生态思想的一项伟大实践,毛乌素沙漠的绿色转变正是这一实践的生动体现。
我想,生态文学是我的一个追求。作品的成功,正是生态思想在故事书写和形象塑造中获得的成功。生态思想进入生态文学,像给我的创作安装了一个助推器,让我的生态文学创作像长了双翼的“神马”,飞翔起来。就因这部作品,我成功地进入了生态文学的行列,这让我备感光荣和自豪。
我想,生态环境保护是现代世界的时代命题,也是未来世界的世纪命题。生态文学是最直接凸显时代价值、历史价值、现代价值、精神价值的文学。以文学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以生态文学记录中国现代化,传播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生态文学担负着从来就没过的时代使命和现实责任。
我想,鄂尔多斯沙漠的治理,阻止了沙漠南移威胁黄河的安全问题,而且,阻止了泥沙流失污染黄河淤积的问题。而今,黄河变清,千年万年没解决的生态环境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变成了现实,这是中国和世界从来没有的先例梦想。
我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给鄂尔多斯带来了无尽财富和福祉,鄂尔多斯实践又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的最好诠释。鄂尔多斯沙漠治理推出许多种植大户、养殖大户、造林大户,甚至企业家,他们以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实现了可持续发展,为中国和世界树立了榜样。
我怎么想都觉得,毛乌素沙漠的消失,鄂尔多斯的变绿,黄河的变清,其变化之大,变化之深远,超出了我们作为一个作家的判断力和想象力。然而,在这浩瀚的沙海桑田的巨大变革中,我们也可以做到的,就是顺应潮流,顺天而为,用自己的笔去记录、见证这一历史性的现代化进程。
《毛乌素绿色传奇》2014年获鲁迅文学奖之后,2017年,联合国在额尔多斯举行世界治理荒漠化大会,发布了《鄂尔多斯宣言》。我很振奋,鄂尔多斯终于走向了世界。
从2011年至今,能够说是我生态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从2014年后,我的文学创作作品有长篇小说《穹庐》,它史无前例以整本期刊形式发表于《十月》,单行本出版后获得长篇小说金榜第一名、“十月文学奖”;生态文学创作作品有纪实文学《精耕库布齐》《我那咏不尽的库布齐哦》和系列生态文章,向世界展示库布齐光伏革命和产业革命。
肖亦农:我也看到了鄂尔多斯再次亮相世界防治荒漠化大会的消息,这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形象的宣示展示。我为中国在世界上树立起绿色形象感到振奋!就像你概括的,中国当代文学从环境文学发端走向生态文学发展,始终与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紧紧伴随。
回顾自己走过的生态文学道路,付出了辛苦,也取得了成果,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进程相比,与当前生态文学发展的空前走势相比,我的努力和写作不过是沧海一粟。尽管如此,我仍然感觉到很欣慰和自豪。因为,在中国生态文学走向繁荣发展的历程里,我尽了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梳理我的生态文学作品,我深感自己的创作历程充满了挑战和收获。每一部作品都是我对生命、对自然、对生态环境的深刻思考和感悟。而现在,中国生态文学创作进入新时代,生态文学热在中国重新勃兴,我感到欣慰的是,肖睿也在生态文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更感到无比高兴和骄傲。
我关注肖睿的创作走向,他的作品不仅走心向内挖掘,抓住了沙漠之魂,更在肆意汪洋的现代抒写中,展现了沙漠的壮丽与神秘。我的创作,沿着郭小川的道路走过来,肖睿的成功,也离不开我们这一代作家的扶持、激励和鼓舞。生态文学道路,就是这样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发扬中走过来的。
我要感恩沙漠,感恩草原,感恩生态。是它们赋予了我们无尽的创作灵感和生命力。在沙漠和草原面前,我们一定要保持崇高的敬畏之心,顺应自然规律,也相信自身的力量。未来,我将继续坚守生态文学的创作道路,用自己的笔和思考去记录、传递、宣扬人类与自然的美丽与和谐。
生态理念是一种文化理念,生态文学是一种审美灵魂,它不仅是种几棵树的问题,它还有一种境界和情怀在里面,而有了境界和情怀,生态文学就斑斑驳驳,灿烂无比。我相信,生态文学注定是构建美丽中国的文化和精神力量。
本网站有部分内容来自互联网,如媒体、公司、企业或个人对该部分主张知识产权,请来电或致函告之,本网站将采取适当措施,否则,与之有关的知识产权纠纷本网站不承担任何责任。